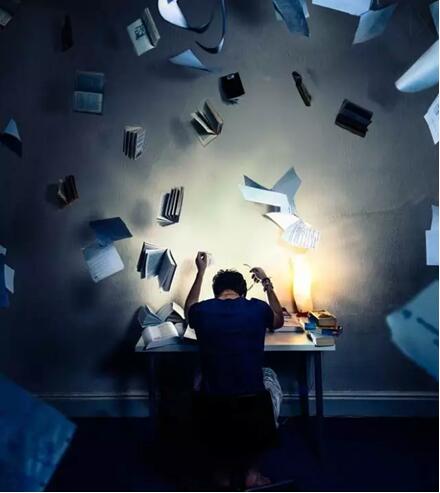总之,小A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带着眼镜的男孩子。走在人堆里不会一眼被认出,但也不至于唯唯诺诺上不了台面。谈不上对工作或者生活的热爱,更遑论专注甚至痴迷于某一兴趣,反正是活着,日子总要过。
文/沈飞地
电话
2017年的第五天,我接到了老高的电话。
老高告诉我,AAwork的初代App刚刚在Apple Store上线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笑了。
我没有对老高说太多祝贺的话,因为彼此都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询问了APP的基本情况后我想起了小A的事,话锋一转,我问老高:
“还准备拍一部关于小A的电影吗?”
“肯定啊,等到选角时你记得来。”
我说好。
小A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北京798参加了一场讨论当代青年问题的小型沙龙。
沙龙的一开始,主持人就抛出了单刀直入的题设:请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尝试共同刻画出当代年轻人的一般形象。要求根据自身的经历和认知,使塑造出的人物最大程度接近年轻人中的“普通人”,以期代表“中间的大多数”。
现场一下子有些沉默,几位大学生最先开始交头接耳,大家经过一阵讨论,依坐次轮流发言。
最先发言的人简单框定了大而化之的形象,越往后去,能被直接描述的特点就越来越少,渐渐的有人开始补缺更加细节的线索。这个看似虚构的人物在我们口中被塑造的愈发丰满立体,到最后简直可以像续写小说一样无限延伸下去。
一轮完毕,又有人举手想补充,从众人脸上的笑容上能看出大家都已经开始有些享受这个“虚构人物”的游戏了。这时主持人及时刹车,宣布还剩最后三个描述机会,之后请大家闭目沉思,在脑海中从头过一遍这个虚构青年的“平生”。
我们暂且把他称为小A。
小A应该来自一个县城,生长在西北的我,布景板自然放在西北,他的家乡便被设定在榆林绥德。
小A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在他们的敦促下,小A从小过着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放假了会跟着表哥去榆林市区耍耍,去过两次太原,没来过西安。
高考那年小A理综发挥稍有不稳,本来梦想的西电泡了汤,勉强上了西邮。大包小包,来到西安。
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在课堂上的梦境游弋和屏幕里的对战游戏中弹指而过,县中的底子犹在,勉强应付得了考试。
大四面对不可回避的选择,舍友四人,出国和考研的两人分别死磕GMAT和数学。小A也不是没有动过这两样心思,布局太晚而显得阵脚忙乱,最后选择放弃,跟着剩下的一个舍友找起了工作。
那年冬天,校招一波接着一波,面对体育馆里眼花缭乱的易拉宝,小A再次没了主意。队伍最长的中电20所和39所自然没胆量去,本地的移动联通分公司似乎又有些看不上,仗着自己还有些学生干部履历,便想碰碰运气去投中兴和华为。
三天后已有同学被通知二面,等到一周后依然杳无音讯,小A知道进研究所是没指望了。已不剩多少选择的余地,得先抓住一根稻草,于是小A进了一家私营空气净化器代理商公司做销售。
起薪2k,提成另算。租的房子在纬一街附近,一户八人的合租房,每天早晨抢着用厕所。当合租屋没收了他的私人空间,频繁的出差又没收了他的私人时间。每月刨去食宿交通开销,剩下的钱刚好只够买一件衣服。
有同学做了房产中介,顺风单多的月份,收入可能是他的三倍;有的同学考进了银行,在柜台前一坐一整天下不来,但却相对体面而稳定。这些小A看在眼里,偶尔忿忿。
路过曾经做兼职的超市,小A想起那年为了攒钱买一部入门单反,在这里干了半年收银。单反到手后开始接些零单,帮学姐拍拍廉价毕业照,后来离开校园没处接活,也就再没闲情拿出来摆弄。
最后,小A应该跟大多数适龄青年一样,多少怀有过一点吉他梦想,也曾跟下台歇场的livehuose主唱聊的愉快。再次路过德福巷的那间小酒吧,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
西安的雾霾又重了,小A戴上口罩,继续往前走。
而在另一些版本的叙述中,小A可能会变得务实些。
他可能会老老实实进了当地的移动分公司,也有可能压线考进了当地的地方商业银行。这样的话小A的日子也许会显得宽裕一些,但故事也会被修正一部分,比如扣除单反情节和吉他情怀,添补上关于购房和婚嫁的烦恼。
这个版本里的小A可能不会偶尔忿忿,代替之的则是偶尔迷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问自己,人生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转头想到明确的购房购车目标,刚刚的念头也就即刻消散了。
总之,小A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带着眼镜的男孩子。走在人堆里不会一眼被认出,但也不至于唯唯诺诺上不了台面。谈不上对工作或者生活的热爱,更遑论专注甚至痴迷于某一兴趣,反正是活着,日子总要过。
你可以跟他谈论任何事物,除了一个叫做创造力的东西。
我们能够顺利拼接出小A的形象,是因为我们身边有着太多的小A,我们见过小A读书时的样子,见过小A工作两年后的样子,见过小A工作五年后的样子。这些样子叠加在一起,自然就出现了小A完整的生平。
当所有人都在沉思中重新梳理完一遍人物形象后,现场依然保持着静默。大家互相张望,有些人的脸上显出了讶异的表情。大概很多人是第一次意识到:被一个不算很小的样本人群定义出的“普通当代青年”,会是这样一种形象。众人的拼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虚构形象的客观性,你又不得不承认,好像真的是这样哦。
沙龙结束后,小A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在那些日常生活中从我身边来来去去的人身上,我总能看到小A的影子,在虚构和现实的来回闪现中,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小A所代表的“中间的大多数”年轻人,正处于集体性自我定位缺失中。
我坚信大多数人的天资相差无几。个体间因为家庭出身、成长环境、经济基础的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后来在眼界、视野、价值判断上的差异。
小A世代务农的父亲无法向他描绘大学生活的美好图样,无法向他传授如何在陌生城市落地生根的经验,在人生选择的几个重要当口,网络信息的爆炸和繁杂适时送出一个漂亮的反面助攻,小A两眼一抹黑,只好随波逐流。
小A那通过自己二十年前的打拼已在城里立足的父亲回首起往事,深感立业维艰,不愿再让下一代从头来过。稳定,便成了小A身上“被赋予的定位”。关乎稳定的工作与成家买房的诉求,代替了本该从初心出发的自我定位。
身处互联网浪潮中的今天,我深感这一切的荒谬。
难道关于自我成长的方法论依然要大半依靠代际传递?
难道海量涌入的资讯终究只能成为越描越乱的信息碎片?
难道那些关于理想、自我、兴趣、初心的坚守依然需要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
小A们在一次次自我选择中错失方向,被时代巨浪裹挟着往前走。而我看到一股巨大的能量正被不断吞噬,这股能量就蕴藏在小A们的体内。
如何尽可能早地让小A们完成正确的自我定位?然后去做他最适合的,去做他最喜欢的,去做他最拿手的。在最符合自身条件的成长道路上充分释放蕴藏的能量,将这股能量源源不断的转化为个人势能和社会势能。
这些思考成了我观察这个世界的新增维度。大多数时候我会一个人静静的想,有时跟朋友分享,却难以得到满意的思想碰撞,往往浅尝辄止。
直到那天,我无意间和老高聊起。
老高
老高是西北汉子,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说起话来抑扬顿挫。老高总说他说不好普通话,我倒觉得是他自找的别扭,每次刚开聊时他还能以普通话相谈,但没过多久便要举手示意,需要切换回方言模式,反正陕西话大多数人也能听懂。我们在这时一般只顾得大笑起来,这个秦腔老陕,倒也真是实在。
老高十多年前在陕西创立长河实业,风风火火一路下来,西北地头可算无人不知,颇有几分当年关中豪杰拉杆子起家的味道。
认识老高好久了,一直把他当成前辈对待,他在传统行业中取得的成功令我侧目,偶尔相聊,多愿意听他谈些人生的经验。然而和老高相处,又并没有太多的拘束感,其实我俩年纪相差十多岁,我却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代沟和话语体系隔阂。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老高读书。老高说他 一年要读300本书,我说难以置信,老高并不直接分辩,只是悠悠的补上了一句:“300本只是保守说法”。
本以为读书人老高在传统行业中修炼得道,只消在西北大纵深里继续扩张他的地产版图,便可稳坐一方诸侯之位。没想到这回老高可让我大吃一惊,秦腔老陕也玩起了互联网转型,不单玩了,还玩的有模有样。
那是2015年年底,我和老高在朋友圈里发现对方也在沪上,正巧晚上都没什么安排,便约在五角场边大学路上的一间酒吧里小饮。
老高先到,坐在靠窗的桌边,我一进门他就向我招手,起初我还真没敢认——半年不见,老高又潮了不少。
三两杯酒下肚,还都在扯些闲话,只是我发现,老高从原先的讲述者,正在慢慢转变为一个倾听者。他更愿意听我说,听着回应着,用他的眼神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尤其对我提到的一些互联网名词,他必定热切回应,对一些专业术语以及英文缩写,居然应答如流。我心下思索:老高号称一年读书300本,想必今年这300本的存量,多半给了互联网书籍。
果然,老高开始慢慢向我询问一些北京互联网圈子里的前沿资讯。他瞪大眼睛看着我,眼神像极了一个陕北猎户。
我直截反问老高,是不是想转型做互联网。
老高默然不语,正好这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在我们领桌坐下,老高对着他们努努嘴。
“你猜他们是哪个学校的?”
“不知道,在这个位置出现,复旦、同济、上财都有可能。”
“那你觉得这三所学校差异大吗?”
“差异自然还是有的:一所超一流大学,一所一流大学,一所二流大学。但现在大学生群体同质化严重,这种程度的学校差异恐怕还不足以在外表和言谈中被展现出来。”
“这就是了,既然我们在酒吧情境中无法用肉眼分辨他们在学历上的差异,那么现在假如把酒吧情境换成面试情境,让你以面试官的身份去面试他们,学历信息依然是不可见状态,这时你该如何对他们进行筛选?”
我被老高的突如其来的问题噎了一口酒精,正在咳嗽间,老高礼貌地递上一张纸巾。
接下纸巾擦嘴的时候,我大脑中已经在飞速的运转:其实老高抛出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抛开“学历”这个相对简单有效的筛选条件,用人方对求职者真正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是岗位匹配度吧。”在我的一阵沉默后,我和老高几乎同时抛出了这个词。我们相视一笑,我见老高,好像又回复到了以前那种讲述者的状态,明显有话要说。我微微颔首,示意老高请说。
老高说他看到现在国内有个巨大的问题,是教育和社会的脱节。
原先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让生在有着巨大人口基数的时代、面对鸿沟般的地区经济差异的我们,获得了相对公平的机会去接受高等教育。而当社会就业压力无限增大,水涨船高,本科文凭早就全部溢出,此时我们的选择是不断增高学历木板,用“考研”设置二道防线,用“考博”设置三道防线,再次用以考察应试能力为主的考试去选拔人才,非等到在二道、三道防线溢出的所谓“精英”,才敢往内引流。
这种方式在今天已经作为被逼无奈而短期内看又行之有效的方式,被用来提高筛选应聘者的效率。
本来一个能力达标的大专生就能胜任的岗位,现在强行要求岗位竞争者必须拥有211院校硕士文凭,才有资格去参加竞争。从大专到硕士,多出的3-4年学习生涯本来应该产生足量的学术价值,而实际情况更多的是用3-4年青春时光换取一个就业入场券。
这3-4年青春时光究竟有多少内耗?是个人能量的损耗,也是社会能量的损耗。这种提高筛选应聘者效率的方式不可谓之不低下。
老高说道这里,我已经开始神游物外了。此刻我满脑子只有两个字:小A,小A,小A。
仿若醍醐灌顶,我立马明白过来:老高所说的几乎完美的和小A构成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从供给端看去,小A们在自我定位中深度迷失,无法最高效的同社会进行对接;从需求侧看去,用人缺口深陷岗位匹配度失真的窘境,招聘方向以学历为杠杆,高开低走。两相叠加,便是对社会资源最大的浪费,无论在个人层面上还是宏观那层面上。
我且先按下自己的情绪,继续问计于老高。
老高说他发现技术是个好东西。很多社会生态中的沉疴顽疾,其实大多源于沟通方式的不透明和数据处理整合的低效,而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这些新技术,恰好能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用这些新技术,去打通人才流动中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诸多壁垒和盲区,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效率,释放社会闲置资源和潜在能量,使每个人的效用价值最大化。
具体地说,假如他有一款App帮助用人方匹配合适的应聘者。匹配的评价体系是不是可以革新?评价参数是不是可以重新选定?匹配的时段是不是可以前置?是不是可以尝试在线上操作“准匹配+培训”模式?
新技术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双方匹配精度和效率的提高必须是跨越式的,不单整块的固定性工作应该被匹配,碎片化的时间同临时性的工作也应该被匹配。这款App的意义就在于动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释放人的价值。
我被老高的描述触动了燃点,以质问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
“老高你一直在从需求端出发,有没有想过供给端的状况?”
“...”
“老高我先给你讲一个关于小A的故事吧。”
AAwork
小A的故事说完了,我们互相看着对方,谁也没有先说话。
老高又叫了两杯酒,叮咚杯响,两人都一饮而尽。
老高说到底从供给端切入还是从需求端切入,他要回去再想想,但是我为他画出的供给端用户画像,他先收着了。他说在他的腹稿里这款产品已经被命名为AAwork,我的虚构人物叫小A,也是有点巧。
“如果从供给端入手,先以强大算法给出私人定制型的成长、就业指导,再用精准匹配提供解决方案,小A们用上们一定会很开心吧。”老高如是说。
我没有接话,而是盯着老高的眼睛。我发现在老高眼里,也开始有了个活着的小A。
“老高,有没有想过拍一部关于小A 的微电影?这样带有人文关怀的人物刻画,也许会引起很强的情感共鸣,而那些能有共鸣的人,应该就是你得第一批用户吧。”
老高笑了。
第二天老高飞回了西安,一个月后老高成立了AAwork试验团队。我继续过着北京上海两地乱窜的生活,偶尔从其他途径听到老高和他的AAwork的消息,我都会想起在五角场酒吧里的那个晚上。
画面切回最开头,挂了电话,我独自走在雾霾天里的成都街头。我想,AAwork和没出世的小A就像雾霾里的成都,只见往前三百米、往后三百米,其他的就再也看不到了。既然到处都是迷雾,那反而又到处也都是方向,无论向哪里走去,即使结果未知,也不妨一试吧。